四月,我來到東部一個靠海小鎮。雖說是小鎮,但以行政區來說,這兒的範圍遠遠超過縣裡的所有村鎮。人們聚在一起,像偌大畫布的棕黑色灰白色點點。八成九成的空間,全痛快刷上深淺不一的綠,波峰起伏,方正連畦。棕黑色灰白色點點,蟻般搬運,生活是列可預期的隊伍,攀過障礙,繞過屋角,一點點就夠過活。綠色站穩腳跟,和藍色商量如何維持畫面平衡。只有鳥不受限制,生翅一族從綠色最高點,飛向黑色電線,沒有規矩。牠們通常在太陽上班前動身,向海或順風。牠們夠輕巧,一眨眼就過去。對著光照,偶爾才能瞥見未消散的淺淺軌跡。若願低頭,也可能在泥土上找到腳印,從凌亂程度判斷,估計早已開完一場晨間或午茶派對。
我是來找朋友的。朋友多年前搬到這裡,開了間小餐廳,只在週末營業,平日裡,他下田上山躺海邊。四月底,我也租了房,學著和鳥一樣早起,和星星一樣沈睡。山色滲入髮絲,海色回歸血液。我漸漸遺忘城裡。在故鄉,高大樓房競相頂著尖刺,比著誰能將天戳洞。每天每天,八小時九小時,切割正好也不正好,模糊的末班車,精準的打卡鐘。滴答滴答滴答——
在這裡,我慢慢放棄屏息的分分秒秒,拾起呼吸片刻,一次—兩次—三次—,深深地做七回,再七回,直到能看見鳥兒真正的腳印。三岔,細緻的尖端,陷在深褐色泥地,附贈兩三片裝飾幼羽。呼—吸—呼—吸—呼—吸—
呼~
五月。從廣播聽到,一場漫天越海的瘟疫,徹底撥亂了城市呼吸。二級然後三級,警戒爬上紅色山頭。過沒多久,孤身走在田間,路過警察遠遠叫嚷:「嘿!麻煩戴上口罩。現在!」左前方的小白鷺和我互望一眼:「叫你呢!」「嘿嘿,不甘我事~」牠輕鬆飛往下一塊田,可惡的鳥。我戴上口罩,立刻就戴。
不一會兒,口罩裡滿是凝結的時間。白鷺群騷動,劃過頭頂朝西去。夕陽正要為夜場搭台。我收拾工具,在水圳旁沖洗泥濘,準備回家。機械馬達隆隆由遠而近,不會又是警察吧?我暗忖。仔細一看,不是警車,是台深藍五門轎車,後車廂大大咧咧地敞開,隨路面顛簸,似嘴一張一閡。正想著該不會是忘了關上,車就放慢速度,順勢臨停。戴著墨鏡和粗粗金鍊的駕駛捲下車窗,問:「你要試吃湯包嗎?」
他沒戴口罩。我滿頭問號。幾隻烏鴉啞啞飛過。該回家了吧。
「試吃...什麼?」
「湯包!小籠湯包!」
下車。關車門。碰!沒熄火吧。敞開的後車廂。漫出蒸氣。湯匙。白色塑膠湯匙。一顆略透明,白色湯包躺在上頭。
「我跟你說,我用料那個皮跟一般不一樣,有加馬鈴薯。那個吼咬下去真的會爆汁,小孩子吃千萬要小心吼,那個不是開玩笑的!」原來大開的車門不是疏忽,湯包哥駕駛座後方,傍著瓦斯、蒸籠。
「好啦,我跟你說電鍋六分鐘,裝半杯水,這樣就好,很快很方便!」
很香。肚子餓。腦子有什麼用呢?我吞下湯包。鹹香鹹香,熱燙汁液滑過喉頭,落進胃袋。忍不住,又嚥了幾口唾液。
你要一包兩包還三包?嗯...你們店名是什麼,之後打電話訂。拿著空的白色塑膠湯匙,我有點尷尬,有點懊惱。
「嗯啊要就現在啦,還宅配這樣不划算啦!」他打開冷凍箱。原來蒸籠、瓦斯桶邊,還有一個很大的冷凍箱。
裝袋。
「一包就好。」
「嗯阿好啦,兩包算你500。」
山邊陰影蓋了一半。天要黑了。生意成交了。
開車門。上車。蹦!滑順倒車。催油門。敞門車消失在暮色中。金鍊子還在我眼前閃耀。
我拎著工具和兩包湯包回家,拿了幾顆蒸來吃。他說多久?喔六分鐘。倚在流理台前,等電鍋跳起來,我回想。從停下到成交,發生好多事,彷彿一場節奏明快的佛朗明哥舞,他舞技大膽絢麗,揚起的裙擺弄花了我的眼。
誰能料到平凡轎車後車廂會出現湯包呢?隱藏於生活夾縫,可居家可出行,彈性就像加了馬鈴薯的麵皮,蒸煎皆宜。我想著。一口咬下湯包,湯汁瞬間爆出。爆漿——令人措手不及,把握精華瞬間,命中目標。當他打開車門,避不開的熱氣蒸騰。我想著,小心翼翼地吃,下一口。
小心翼翼。口罩下人們漸漸適應新的節奏。七月。延長的三級是熱燙海岸線。八月。下了好幾場大雨,今年的蛙似乎叫得更大聲。九月。我看見蜻蜓飛了滿天,薄翅的牠們據說能穿越萬千公里,從這片海到那片海。三級還沒變二級,我決定回城裡探望生病的阿嬤。
那天傍晚,接到媽媽來電,說這次病得嚴重。我立刻買了最近的票,衝到月台,口罩內快速累積,吁—吁—吁—。急也沒用,如果我是鳥,或者蜻蜓——月台上連我在內,只有三個人,看不清臉他們的臉。太陽要下山了,誰阻止得了?我來回踱步,延伸到遠方的鐵軌,悄無聲息。為了分心,我走到佈告欄,什麼都好,閱讀文字讓我平靜。然後我看見一張通緝告示:一張男人臉,沒有墨鏡,但有金鍊子,鼻子和嘴。心頭一震——
打開手機。關鍵字。新聞報導:「五月十日,男子疑似因債務糾紛,以繩索勒斃同居人後分屍。目前在逃。屍體仍未尋獲。」
台鐵響起火車誤點的廣播。
我想起躺在冷凍庫裡的小籠湯包。噴汁肉餡,以秘方包裹。還剩半包。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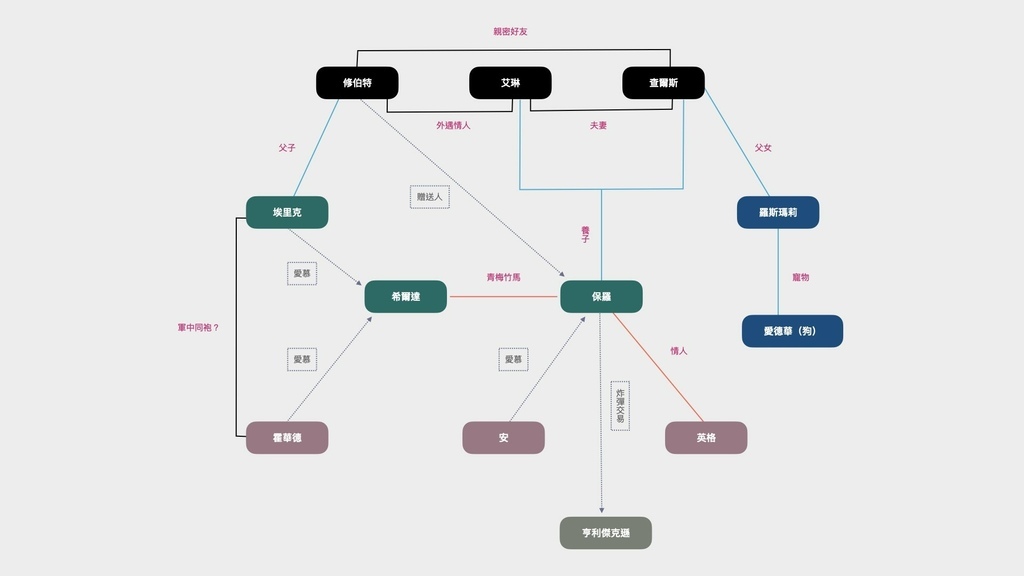

 {{ article.title }}
{{ article.title }}